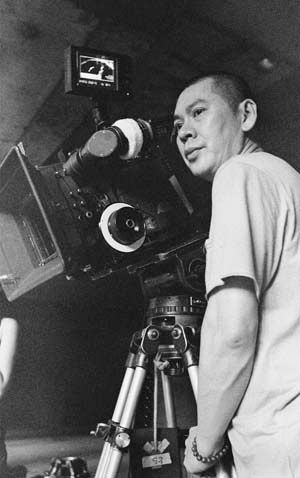
林:什麼樣的關連?
蔡:流浪、漂泊。因為莫札特也是六歲就開始全歐洲跑,其實也等於是對貴族、皇室做流浪藝人。我就想到這個流浪【的主題】,所以你看我最後用的一首歌,我覺得都是巧合,也不是故意的,你去查歌名,那首是卓別林寫的音樂「灰街燈」,跳芭蕾舞的那個。那個電影有音樂,就是他寫的這首音樂,很有名。這首音樂我很熟,是因為李香蘭唱的,我喜歡李香蘭。
當時在馬來西亞拍的時候,還沒有開拍,我也沒有想要用這首歌。是無意間聽到一個人家送我的馬來西亞歌手的CD,他唱老歌,我就覺得這個人的聲音好好!結果唱到〈心曲〉的時候,剛好我在車上,我跟湘琪都很感動,說這個音樂好像我們的電影!後來就把音樂拿掉,只剩下聲音。所以你看是一個巧合,就都是流浪漢。所以我覺得很奇特,所有的東西都這樣慢慢拼湊起來。
林:影片中的華人雇主是在馬來西亞實際生活裡很普遍嗎?他們主要是香港過來的移民嗎?
蔡:普遍。那種店是很普遍的,但是也在沒落中,也在轉型。很多都做小販這種型的。基本上,這種茶室還有。我拍的是真的茶室,只是樓上已經沒有人住了(店老闆住樓上)。事實上以前都是茶室的家庭,樓上還租給別人。他們不是香港移民,是早期的移民,應該有三代以上了。就是福建、廣東、潮州最多,就像我家鄉一樣,還有客家。這些人很多是海南人,他們做餐飲業的。
吉隆坡有一區,我們叫做茨廠街,整個區幾乎是中國人的,有點像迪化街這樣子,我們也叫他做China Town(中國城)。整個茨廠街幾乎都是華人活動的地方,但是馬來人和其他種族也會到那裡,因為吉隆坡【族群】比較融合,就是各民族比較混合在一起。當然現在多了非常多的外勞,你到禮拜天、假日,其他人都關門了,就是全部是外勞在街上,像香港那樣。
那些做外勞生意的店都是開著的。茨廠街最大的變化是什麼,就是華人陸陸續續搬走,那些店有的就拆了,有的還在。在的有些還在經營,大部分是租給了印度人,印度的老闆,他們拿來做外勞的生意,比如說自助旅館或是餐廳、孟加拉的餐廳。一般當地人是不知道裡面變什麼樣子的,雖然他們每天走過。像我這種才會知道,因為我要去看各個外勞。
像我拍他們兩個人上廁所的那個房子,樓下也是個咖啡廳,是一對夫妻經營的,但我沒有拍。他樓上就租給了這些外勞(他們是從後面進出),是真正的外勞。所以我沒有改。像那個蚊帳也是外勞的蚊帳,他們也有演出,住在那個房間的外勞。
 林:在你的片子裡面,有很多象徵意義濃厚的鏡頭,在這部影片尤其如此。例如小康同時就是演雇主的小孩植物人,意象這麼鮮明、強烈,還有像片中的床墊搬來搬去,以及裡面那個水池。請你談一下這些意象。
林:在你的片子裡面,有很多象徵意義濃厚的鏡頭,在這部影片尤其如此。例如小康同時就是演雇主的小孩植物人,意象這麼鮮明、強烈,還有像片中的床墊搬來搬去,以及裡面那個水池。請你談一下這些意象。
蔡:我這部電影其實比較跑到一個比較哲學的意味裡去。我五年前對外勞跟政治的議題很感興趣,五年後我的心境也改了。我覺得也蠻好的,如果我當時拍,絕對不是這個樣子,可能會更寫實,會更符合一般人的期待──就是要回到馬來西亞拍外勞的東西,大部分的人都有這個期待。但我覺得我應該更寬廣一點,把他們當作不一定是外勞,我沒有在電影裡面有任何清楚的指示他們來自哪裡,但是你起碼知道是工人。(有老外甚至說陳湘琪會不會是他的女兒?我說你會看成這樣我也沒有辦法了。)這是我電影的特質,沒有太多明顯的提示,所以基本上可以有各種解讀,但是我的確是以他們作為藍本。
這個電影,我覺得是比較走到精神層面,也就是說其實已經不是單單在講外勞的問題,他比較在講人的困境,人和環境的關係。比如說,那個煙害是最明顯的,你無處可逃。那個房子將要被賣掉,它的命運也有可能要被拆掉,老板娘捨不得,可是她的堅持也可能很不穩定,她也會迷失、也有她的負擔──兒子跟房子。
如果說每個人都有一個牢籠的話,他的牢籠就是那個店、她的過去、她的小孩拖著他。所以她也會偷吃(好奇那對男女要幹什麼)。可是她最後好像也是有一個權勢的【象徵】,像他在控制陳湘琪的手。可是她也被整個大環境所控制,最後迷失了。我覺得這些都很象徵,包括場景,包括那些物體。
林:片中大樓裡那潭水對你最大的吸引力是什麼?那個景象很令人震撼。
蔡:那個【景象】當然我一進去就是震撼。想像不到積水積成這個樣子。我們問過如果要抽掉那這水的話要抽多久,他們說至少一年。如果用很多很多機器抽的話,可能抽半年。其實不只是這潭水,還有這個樓的其他地下室,全部都是水。像寶珠走的那個樓梯也是水,是連在一起的。其實這個建築我在99年就對著它了,可是我沒有走進去,因為它已經被封了。
那時候我還在寫劇本,沒有往裡面走,還沒有拍我通常就不會進去,我就靠想像,然後寫,可是我從沒有寫到那潭水。後來等到今年我進去的時候,看到這潭水,我當然很興奮,覺得太棒了。
同時,我想到這個水的意義,它其實像一個湖,像一個心湖,每一個人心裡面的湖,死水。我想到李香蘭的歌,心湖,死水起了波動。基本上它不動的,很黑很髒。
我又想到詩人北島的詩,特別喜歡他寫的「我們沒有失去記憶」,就是說基本上我們覺得我們都失去很多記憶,其實我們沒有,它是藏在心裡,我們要去找我們心裡面的湖。我覺得整個電影好像在追尋一種意義。
生存的意義在哪裡?
人和人之間最單純的關係在哪裡?我覺得是這個電影裡面最強烈的一個需求。所以你會看到我在處理每一個人,都會有一點互動。
 林:影片裡諾曼的馬來人角色形象是非常正面的人,就是完全無私的付出,最後卻發現他被背叛了。這樣的一個形象是否刻意美化要傳達某種訊息?
林:影片裡諾曼的馬來人角色形象是非常正面的人,就是完全無私的付出,最後卻發現他被背叛了。這樣的一個形象是否刻意美化要傳達某種訊息?
蔡:基本上我對這個角色最先想到他是一個窮人,他一無所有,雖然他有住的地方(可能小康才是一無所有,可是他其實也差不多了)。他撿到一個床墊那麼爛,他也很高興。還有他對著那個湖,他的工作是對著那面死水,要抽那個死水。
這樣的一個人,你不太知道他心裡想什麼。可是我覺得,就是因為這種一無所有的感覺,所以他更沒有負擔,他對人的關係,他不覺得他的東西會被人家偷走,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人家拿走,所以他反而很開放。當然他也有更深層的東西,也有藏了很多內在,這個電影在拍的時候我其實也在拿捏說,他們之間有沒有性關係?要有這個嗎?還是不要有?我後來想【如果】有,就是為了要討好觀眾(笑)。
有,太容易有了。
我常常覺得說,我拍電影比較辛苦的一個地方是,我都想什麼才是對的,什麼才是更深的?而不是隨著觀眾,這個很過癮、那個很過癮。我不會這樣想。一方面年齡也比較成熟了。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有一點像我父親的朋友,他們之間的關係很好,是好到太太都不太重要那種,可是什麼都不說的。我父親這個朋友去年過世了(他們兩個現在都過世了),我們在他還沒死之前還去看他。我永遠會覺得說,他們的關係是一種很奇怪的關係,男人和男人的關係。
就像我跟小康的關係,也是一種很特別的關係,沒有什麼要求,沒有什麼忌諱,什麼都沒有,很簡單,你就是很疼這個人。我覺得諾曼更不用說,每個人都可能有這種關係。諾曼是一無所有,當他擁有這張床的時候,他不可能帶一個女人回來,帶一個男人也好。諾曼本身是他的特質,他所呈現的,基本上是我對他是很短的時間裡面認識的…。